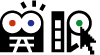轉貼:友子的情?
原作:艾小柯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甚至都已經該忘記怎麼稱呼你了,我也不知道這封信,究竟該從何說起。年輕的時候我曾經強迫自己不去想你,後來我便真的很少想起你。現在,我戴著花鏡慢慢給你寫信,很陌生。
終於再想起你是有一天,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籮筐裏揀著檳榔,鎮子裏的人都去聽演唱會了,街上很安靜。傍晚的陽光斜斜的照進來,潮氣慢慢蒸上來。我放下籮筐,活做久了,手腳都有些冰涼。我慢慢的扭頭——我已經老了,腿腳都不大方便——窄窄的長條凳上放著一個長方形的漆盒。我不知道是誰,什麼時候來過放下了這個盒子,我周圍一個人影都沒有,只有風偶爾吹過樹葉沙沙的響。我打開盒子,裏面竟然是六十多年前一張我的黑白照片。我愣住了——少女的我看上去那麼單薄,羞澀又稚嫩。我的裙子在照片裏輕輕揚起來,背後的大海沒有風也沒有雨。照片的下面是你女兒的來信,還有七封沒有寄出的情書。
我猶豫了好一會兒才敢拆開那些信,借著馬上就要暗下去的天光,仔細又吃力的讀你的筆跡。你怎麼一下子就提到那個日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已經老了,很多事情都記不清了,很多事情也不願意再記起。我的心臟不該跳得這麼快,這讓我很難受,眼前的字跡也模糊起來。我站起來,抱著盒子進了屋,坐在竹椅子上發呆。
我不願意想起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我一個人,戴著醒目的白色針織帽,一清早便從家中逃了出來,提著笨重的行李,站在人潮中孤獨的等你。你的船鳴笛了,離港了。我周圍的人們都在歡呼,都在揮手致意。我像一個傻子一樣提著沉甸甸的箱子,頭腦裏如同爆炸了似的有無數的聲音在嗡嗡響著,可我卻什麼都聽不清。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我抬頭,黑色的天幕裏繁星一點一點,周遭靜悄悄的,我不知道自己該向哪里去。我摘下帽子,扔了箱子,蹲在無人的碼頭上哭。你就這樣走了嗎?沒有一句告別,沒有一個解釋,什麼都沒有……
我是那麼的恨你,我恨你的民族,提著槍炮佔領了我的家鄉;我恨你的國家,把我同胞的血染遍曠野;我恨你,從海的那邊來到這片遭受屈辱的土地,用勝利者的語言剝奪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自由!可我又是那麼愛你,我愛聽你講天上的星星,你在黑板上畫出太陽系行星排列的順序圖,你知道春花為什麼會開放,葉子在秋天為什麼凋零,你說世界很大很大,海的那邊是另一片大陸,海的盡頭有晶瑩的雪花和凜冽又溫柔的冬天。你愛孩子們的笑容,你說北海道的孩子與恒春的孩子都有一樣純潔的眼睛。啊,我恨你,我恨你的民族,我恨你的國家,但是我又愛你,愛你的憂鬱,愛你的沈默,愛你所嚮往的,那如同天國光輝般的自由!
你終究是一個懦弱的男人。你走了,我老了。
我在昏黃的燈下讀你的筆跡。你說海風總是帶來哭聲,愛人哭,嫁人哭,生孩子也哭。那麼,你可曾聽到海風中,我獨自哭泣的聲音?
我托著沉重的行李回到家,我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我是一個失敗者,我依然幻想自己的心隨著你,在看不見邊際的黑色海洋之上,駛向永恆的遠方。媽媽的眼淚讓我心碎,父親的沈默讓我內疚,我把自己關在狹窄的小屋裏,只是癡癡的望著遠方的海。你歸鄉,我也歸鄉;你離鄉,我也離鄉——我的心還不如父親的小小舢舨,在十二月的海上,被狂風暴雨打成一億碎片,我的眼淚都化作了泡沫,在蒼茫的天地裏再也沒有了故鄉!
我恨你,我要忘了你。六十年裏我再沒離開過恒春,我要用一生的勞累來補償我對這片土地的背叛,我要用一生的時間來忘記你。我曾經嚮往遠行,但我嫁了恒春本地的漁民,他的氣味就如同我的父親,而我也像母親一樣,永恆的守候在海邊,等待他的歸期。年輕時我只想離開這土地,去海那邊的大陸,大陸那邊的海,去體會究竟什麼是你說的天國的自由。但我在恒春守候了六十年,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熱愛這生我養我的小小島嶼。我常常去海邊散步,我喜歡坐在礁石上聆聽海風的嗚咽。我是孤獨的,我的愛情就埋葬在這洶湧的海水之下;但我又是幸運的,我留下來,我為他補魚網,我在小廚房裏混汗如雨的準備一家人的晚飯,落山風來了我坐在巷弄裏剝洋蔥,我泡濃濃的港口茶,我默默的聽老月琴彈奏出思想起的調子,我有了兒女,我終於知道,我的根在這裏啊,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我搬離了海角七號,我已經將青春歲月埋葬在了故鄉的土地。冥冥中究竟是誰,把這遲了六十年的情書又交到了我的手裏?我在清晨的薄霧裏摩梭著你熟悉又陌生的筆跡,我一遍又一遍的讀著 “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我已經老了,我的眼角滿布皺紋,我的心臟已經不能承受那麼沉重的眼淚。我明白,又不明白。我愛你,我恨你,我不原諒你,但為什麼,我早已乾澀的眼角,卻越來越濕潤?在這個安靜的夏日清晨,我突然渴望起落山風來,我渴望十二月海洋的哭聲,我不由自主的想像你在輪船甲板上就著微弱的燈光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書寫的樣子。天該是黑色的,海也是黑的,晨曦還沒到來……
我的孫女就出生在這樣的夜裏。她的模樣跟少女的我一模一樣,她是那麼單純,活潑。她喜歡問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她想要知道海那邊的大陸究竟是什麼模樣。有一天她告訴我,她愛上了一個海那邊的男人,她要跟著他去尋找新的故鄉。我祈求她,我威脅她,我禁止她離開她真正的故土。我知道,是我不再相信愛情,我恨你,我恨你的民族,我恨你的國家,我不能將我最好的希望交給你們來親手毀滅!年輕的她也如同六十年前的我,眼睛裏有海洋的清澈,也有海霧的迷蒙。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走的,沒有告別。六十年前,一場戰爭將我和你隔在了海洋的兩端;現在,卻是我,隔在了她和他的兩端……
我終於明白,海洋,為什麼苦澀得叫人皺眉。這片海水中埋葬了太多的愛情,接納了太多的眼淚,承載了太多的思念。落山風在哭,海潮在嗚咽。生哭,死哭,青春也哭,白髮也哭。時代的漩渦裏啊,究竟哪里才有將思念連接起來的彩虹?
我已經老了,皺紋爬滿額頭,白髮稀疏,兩眼渾濁。我無法想像你去世前的樣子,我曾經那麼的愛你,那麼的恨你,我還是那麼的愛你,那麼的恨你;但我希望你在最後的一刻兒孫滿堂,安祥平和,我希望你在絕望之後終於找到了希望,就好象我在離鄉之後終於找回了故鄉。恒春是我的根,是我一輩子的愛與思念;而海那邊是你的祖國。我終於明白六十年前的你為什麼要獨自離去,原來你早知道,我們最不能舍的,都是對腳下那片土地最原始最純粹的愛啊。
六十年前,島嶼之間的海洋容不下我們小小的愛情,海風的嗚咽吹散了我們最為深切的思念。六十年後,如果真的的有天國,如果人間的希望真的存在,那麼,就讓這封遲到了六十年的回執化作彩虹吧,在生命的盡頭,我只想要看見藍色的海洋,清澈的風,也許,也許還有孩子們最純真的笑臉,還有你輕微而自由的歎息。
主題:友子的回信
無圖示
艾小柯
文章日期:2010/4/22 16:51
文章點閱: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