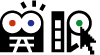以下是《電影筆記》在去年坎城影展時,針對侯孝賢跟茱莉葉畢諾許 (Juliette Binoche) 所作的專訪。有四分之三的部分,本人已經為電影資料館電子報翻譯過;本篇是將剩下的四分之一全部翻完,所以是完整版。
不過,《電影筆記》的前言我就不翻了。
侯孝賢:我從未曾想過有一天我會來到法國拍片,尤其是在日本拍《咖啡時光》(Cafe Lumiere) 之前更是無法想像,我根本沒想過要到外國拍片,因為對我來說,熟不熟悉一個地方的現實性實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以致我還沒能夠把我自己「國際化」起來。這是所有事情的基礎。一直到二○○三年為了要向小津(安二郎)致敬,有人向我建議到日本拍片,在這之後,我才瞭解到原來到外國拍片根本是有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事,所以我也是抱著喜悅的心情欣然接受奧塞美術館 (le Musee d'Orsay) 給我的邀約,我樂見其成。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很瞭那個地方,所以他讓我渴望把原來的短片計劃拍成劇情長片,跟他一樣!(譯註:奧利維耶阿薩亞斯拍過紀錄片記錄侯孝賢,他把侯孝賢當作導師,因此他們兩人是熟識的。)
畢諾許:當我第一次跟侯孝賢見面的時候,我看過他的三部片──然後,我又再多看了幾部。對我來說,《紅氣球之旅》讓我再發現到「自由」。當我跟韓內克 (Haneke)、齊士勞夫斯基 (Kieslowski) 或其他英、美地區的導演合作的時候,拍片工作真的是分毫都要計算清楚……跟著侯孝賢工作,改變了我對我的「事業」的看法──如果是以一條路的意義來看「事業」這個詞。所有這些,都跟喬治桑 (George Sand) 寫過的一段關於「未來的演員」(l'acteur futur) 的話相符,初夏(二○○七年)的時候我已經把這些文獻給給《電影筆記》了(參見第六二五期)。「未來的演員」就是他(她)自己的作者,他自己的導演以及他自己的演員;對我來說,是這種演員才能拍得出未來的電影。
侯孝賢:首先我會先跟人們見面,此時我根本都還不知道將來會不會跟他們一起合作。茱莉葉給我的立刻的感覺是,她並不「演」她自己的演員事業,反之就像一張白紙我們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塗上顏色。跟她見過第一次面之後,又再回到巴黎,我才見到西蒙 (Simon),影片裡的那個小男生,然後也在找劇情女主角會居住的公寓用以拍片。製片弗杭蘇瓦馬勾藍 (Francois Margolin) 他的公寓,我很喜歡,因為這公寓裡面有樓中樓。所以在現場我又想出一些新的點子,然後,也就不再離開周邊的環境:想到西蒙唸的小學、他喜歡去的菜市場……
回到台北之後,我繼續編寫劇本;就在這段期間,我閱讀了一些曾經住在巴黎的外國人所寫的書,特別是美國記者亞當果普尼克 (Adam Gopnik) 的書《從巴黎到月亮》(De Paris a la lune),以及另外一篇文章講到怎麼樣搬鋼琴的故事。《從巴黎到月亮》這本書有講到阿耳貝拉摩黎斯 (Albert Lamorisse) 的《紅氣球》(Le Ballon rouge) 這部片,就是這樣我才發現到這部片。寫完劇本之後,我回到巴黎,跟著茱莉葉在一家中國餐廳吃飯。一位侍者走過來先讓我們看一下等一下準備要被下廚的活魚,她(茱莉葉)可是表現得興奮異常!但當時的她還不夠接近我腦袋所構想的那個角色。到某一刻她跟我談論(約翰)卡薩維茲 (Cassavetes),我才感覺到,是的,她已經很接近那個角色了。
畢諾許:是的,當我在看《受影響的女人》(A Woman Under the In- fluence) 的時候(譯註:約翰卡薩維茲導演),我才茅塞頓開:我的角色,應該要是一位處在完全的混亂中仍然能夠昂首無畏的女人。通常在開拍一部片之前,我們要找到一個能夠跟導演比較親密的氣氛;但每一次我們必須要相見的時候,總是至少有十個人同時在餐桌上。就在這幾次的會面中,我們總是因為某些殘言片語修改劇本(譯註:畢諾許用雙關語:複數的 bribes 既可以指一個整體的片段,也可以指剩菜剩飯),像他(侯孝賢)就問我說:「妳希望這個角色要叫什麼名字?」「蘇珊。」「妳同意要變成金頭髮嗎?」「好呀!!!」
在劇本裡面,重點是放在母親(我飾演的角色)在很多場合都缺席不在,因此那時候我根本不太清楚我應該佔有什麼地位。不管怎樣,那時我是知道我們沒有一個已經固定下來的劇本,因此我們都必須創造一個角色,給這個角色一個專業的熱情,給她設定一些衣著……等等。有一組中國人(華人)的工作團隊來到我的房間,挑出一些是屬於我的衣服(但我自己卻從未穿過),這點子還挺不錯的。
侯孝賢:我其實有點希望她能夠稍微修改我最初發想出來的點子,我永遠都接受她提出來的建議。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但是髮型(或髮色),這可是我想的。
畢諾許:這個角色,其實是有一塊已經焦灼的一面,跟她自己比起來也是有一點落差,彷彿也就是一個木偶(布袋戲)。侯孝賢比較喜歡一位原本是黑頭髮的金髮女郎(譯註:畢諾許用『根源』(racines) 的意思或許也包含說原本是黑頭髮的金髮女郎其髮根都還有些黑色的感覺),而不是一位絕對完美的金髮女郎,因為這種人沒時間把她的頭髮換成另一個顏色……
侯孝賢:我還是比較堅持木偶的意念,特別是這一位文人能夠把海水都蒸發掉。當《電影筆記》要求我做某件事要向楚浮 (Francois Truffaut) 致敬,我就已經揭露過這段故事,因為我想要談的是很堅持己見的角色(們)。
畢諾許:一剛開始,蘇珊就被設定成是木偶師傅。我父親是雕刻家,他會做一些面具提供給劇場使用,所以我一直都跟這圈子很接近。我當然是有看過《戲夢人生》(Le Maitre de marionnettes),然後侯孝賢的翻譯帕思卡兒戈伊諾 (Pascale Guinot) 寄給我一些文章、一些書讓我看。然後我跑去看菲利普冏提 (Philippe Genty) 的表演,我邀請一些木偶師傅到我的庭院裡表演玩偶/扭偶 (guignols) 的戲……(笑)侯孝賢讓我再放慢一些節奏。但是在開鏡前三個禮拜,他跟我說:「我們要弄出一齣木偶戲。」這工作最主要是要把本來是中國的故事改編成法文發音的木偶戲。雖然在電影裡面只能看得到一些片段,但這齣戲是真的存在,前後表演了大約二十分鐘。侯孝賢跟我說:「妳不能配所有的音吧,頂多妳只要配一、兩個角色的音就好了。」然後我說:「不行,我要配全部的音!」因為,很多年下來,其實我每天晚上都是這樣子做,因為我會跟我的孩子們講故事。我們只是要排練一下聲音,純粹只是試試看而已,但侯孝賢已經到場了,沒跟我們預先告知就已經拍下我的練習。
侯孝賢:剪接的時候是有些複雜,我總共剪了十個版本,而且我特別後悔沒有先把每一個毛片加上字幕。但相反地,拍片的過程是相當緊湊的,我們只有六個禮拜的時間拍;我曾想再回到某些地方,但我們已經往前行了,所以每一次有人提醒我說西蒙人在浴室或是在上面,其實飾演西蒙的小男生他已經待在學校。最後,剪出來的影片其實很像拍片拍出來的東西(譯註:這是指侯孝賢拍出來的畫面幾乎都有被剪進完成版裡面;很多導演常常拍出很多場景,但最後都會因為片長的關係不得不刪除某幾個場景;這就是侯孝賢所說的剪接完成版很像當初拍片計劃中已經安排的場景順序)。在剪接的時候,我刪除最後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中,茱莉葉跟西蒙在電腦前面觀看一些家庭影片,茱莉葉哭了,因為她開始理解到她跟她兒子之間的關係有哪些東西是她沒做到的。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場景,但實在太過「總結」的意義,不夠開放,而且我也不是故意要讓觀眾掉眼淚。我比較希望觀眾們能思考。
畢諾許:侯孝賢跟他的攝影指導以及他的錄音師一起合作,其實是運用了某種程度的工作方法,這種方法能夠讓在鏡頭前面發生的一切都有了非凡的意義,因為它讓拍片的時刻給人諸多尊重,也能讓人全神貫注,讓我們能夠忘記了我們自己,忘記了別人正在看我們的目光。這種相當輕盈的空間,就像是小孩子許的願望:我們所有人彼此都有關連,如果沒拍成功,真的沒什麼關係;而且如果拍得好的話,其實也還是沒什麼關係!
訪談者:尚-米歇弗侯東 (Jean-Michel Frodon)、夏洛特軋松 (Charlotte Garson);
翻譯(中翻法):帕思卡兒戈伊諾 (Pascale Guinot);
訪談時地:2007 年 5 月 23 號,坎城 (Cannes)。
翻譯(法翻中):周星星
參見周星星部落格:http://blog.yam.com/jostar2
主題:侯孝賢、畢諾許《紅氣球》之《電影筆記》坎城專訪
無圖示
周星星
文章日期:2008/5/7 16:50
文章點閱:830
此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