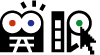金馬獎秘書長解密李安 幾十年細說從頭
[選稿]盛于藍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6-03-17 14:48:21
李安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頭上籠罩著華人之光的光環。光環下的李安和生活中的李安有何不同?本報特邀請臺灣電影金馬獎秘書長王清華先生採訪發掘李安的伯樂徐立功、李安的大學老師、李安和妻子的朋友、《臥虎藏龍》的編劇,共同為我們勾勒出李安的側畫像。他的婚姻、他的為人、他的性取向,都在話題之中。
李安第一印象:“李安”是藝名嗎?
十多年前,我有一天下午到“中影公司”,在製片部看到一位陌生人。我問中影的朋友:“那是誰呀?”中影朋友回答:“一位新導演,叫李安。”
我又問:“李安?是藝名嗎?過去沒聽過。”朋友答:“搞不清楚是藝名還是本名。”
這是我對李安的第一印象。老實說,第一印象沒什麼印象。
1997年10月,臺灣的“影評人協會”有8個人參加第二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蔡國榮夫婦也是其中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對這享譽已久的“十裏洋場”,大家都倍感新鮮,不免到處走走看看。但在所有活動中,蔡國榮夫婦除了與我們去“王寶和”吃了一次大閘蟹外,幾乎都待在旅館裏,足不出戶。
我不免好奇,問他在忙些什麼?
只見他神秘兮兮地說:“在趕一個本子。”
我說:“趕劇本在臺北趕就好了,幹嗎大老遠跑到上海趕?”
他沒正面回答我,反問了我一句:“王度廬的作品你過去有沒有讀過?”我問:“哪一部?” 《臥虎藏龍》!
沒想到,這與李安有關。
再見李安:已是知名導演
1998年的夏天,蔡國榮約我與曾西霸下班後到“京星”去飲茶。那時我還在《臺灣新生報》上班,蔡國榮在《中國時報》編影劇版。晚上12點,“京星”裏高朋滿座,我第二次見到李安,也許是晚上,他穿得很輕鬆。這時,他已是知名的導演了。我們邊吃邊聊,但大部分的時間,李安都是靜靜地聆聽著,他的話不多,偶然說上幾句,也都是要言不煩,沒有什麼“嗯、啊、我覺得、似乎是”等等之類的廢話。但千萬不要被他的外表所騙,以為他不會堅持己見,或偶爾人云亦云。
對此,蔡國榮就說:“李安導演外表謙和,個性看來十分溫婉。但其實他並不是如他外表那般,可以輕易說服他或改變他的想法。“在籌備《臥虎藏龍》的時候,他雖然初次嘗試拍武俠電影,但他其實蠻有想法的,而且對很多觀點或看法是很堅持的。因為他個性謙虛溫和,因此往往又表達得不是很明確,對編劇而言,就增加了琢磨的功夫。”
蔡國榮坦承,那段時間,為《臥虎藏龍》的劇本,確實溝通得很辛苦。《臥虎藏龍》最早的劇本架構,大約都出自蔡國榮之後,特別是他把那個捕頭“一朵蓮花”劉泰保的角色做了調整,讓三位主角的戲得以凸顯,功不可沒。然而,《臥虎藏龍》正式上映時,編劇變成了“王蕙玲、詹姆斯、蔡國榮”三個人,不僅多了兩位,裏面還有個外國人,蔡國榮在順位上變成了“第三者”,這一點,蔡國榮始終不願多做說明。
《臥虎藏龍》的“最佳外語片”始末
《臥虎藏龍》在2001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及“最佳藝術指導”(葉錦添)“最佳攝影”(鮑德熹)等獎。對臺灣而言,最有意義的當然是“最佳外語片”這個獎項。因為其他獎項的報名、入圍、得獎,都是發行公司“哥倫比亞”報的名,只有“最佳外語片”是中國臺灣報的名《臥虎藏龍》那年能代表臺灣報名奧斯卡角逐並得獎,與我大有關係。
臺灣每年都會找幾位元與電影有關的人士,選一部當年的臺灣電影報名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2000年11月的某一天,電影處找了電影導演黃玉珊,電影學者曾連榮、劉立行,還有文化評論者謝鵬雄及筆者五人,在下午五時半左右於“新聞局電影處”碰面。負責這項業務的科長是陳德旺。大家先吃完了便當,就在一張小方桌前展開討論。那一年共有三部影片被提出來角逐:張作驥導演的《黑暗之光》,中影公司出品、柯受良主演的《條子阿不拉》及李安的《臥虎藏龍》。
第一輪投票,《黑暗之光》兩票(黃玉珊、劉立行)、《臥虎藏龍》兩票(曾連榮、王清華)、《條子阿不拉》一票(謝鵬雄)。
《條子阿不拉》先淘汰出局。
接著開展第二輪投票。投票之先當然還要有一番討論,那時,整體形勢是傾向《黑暗之光》的。一方面是《黑》片非常“本土”,講的又是弱勢盲人的故事,同時又已經得了一些獎項,聲勢正盛。 我當時說:“《黑暗之光》的導演張作驥是我的好友,我當然認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若論‘奧斯卡金像獎’的屬性,則《臥虎藏龍》的題材與表現方式,應該比較容易獲美國人的青睞。”劉三行老師聽我說完後表示:“清華兄這個論點,我可以接受。”
第二輪投票結果如下:
《黑暗之光》兩票(黃玉珊、謝鵬雄)。
《臥虎藏龍》三票(曾連榮、劉立行、王清華)。
《臥虎藏龍》於是代表臺灣報名參加了奧斯卡,並得了“最佳外語片”的殊榮。
牯嶺街少年和李安太太的娘家人
我與曾西霸老師在1964年時,都在臺北市羅斯福路上的“老成補習班”實習,准備考高中。那時,兩個毛頭小夥子下課後,常牽著腳踏車,漫步在附近牯嶺街的舊書肆,高談闊論,構築著年輕人的美夢。
好多年後,曾西霸才向我提到一件事,他說他那時中午吃完便當後,就會跑到他哥哥的公司去,喝碗綠豆湯,真是好不羨煞人。 他哥哥叫曾西江,公司就在離補習班不遠的牯嶺街上。合夥人則是李安的丈母娘。曾西霸回憶說,李安的老丈人在經濟部服務,經濟部就在南昌街上,離補習班、牯嶺街不遠。李安丈母娘與曾西江合開了一家“鑽探工程公司”,以地質實驗等業務為主。這家公司一直到五六年前才結束營業。
李安的丈母娘一共生了一男三女,李安老婆林惠嘉是最小的女兒。曾西霸說,林惠嘉最像她媽媽。當時,曾西霸才17歲,林惠嘉大約剛念小學,小曾西霸幾歲,但因跟著曾西霸的哥哥曾西江叫“叔叔”,而也叫曾西霸“曾叔叔”。 那時林家一家住在臺北市埤腹路(當年叫和興路)的經濟部宿舍裏,曾西霸是少數去過她家的人,所以幾乎是看著她長大的。曾西霸也是少數因李安的太太而認識李安的朋友。
婚姻是否曾經亮過“紅燈”?總是難免會有的啊!
說到李安的太太林惠嘉,媒體都把重點放在李安在紐約的那段歲月。當時李安無所事事,不問家計,每天抽煙、看報、喝咖啡,十分苦悶。養家活口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老婆林惠嘉的身上。這段長達六七年的時間,對李安而言,雖然是“不堪回首”,卻也蘊積出李安的能量。當這些能量一旦釋放出來,也就沛然莫之能禦了。
很多人問到李安這一段,李安總是以一貫的態度笑笑。至於老婆有沒有怨言?婚姻是否曾經亮過“紅燈”?李安也仍然是雲淡風輕、四兩撥千斤地一語帶過:“總是難免會有的啊!”李安太太是學“生物”的,跟搞電影整日埋首劇本中的李安,當然難有交集。而且她對電影工作幾乎是毫無興趣。李安在紐約拍《推手》、《喜宴》,老婆、孩子、自己都粉墨登場,軋上一角。不是因為老婆孩子愛出風頭,純粹是為了省錢省事。李安太太對電影的“外行”,從李安與曾西霸很私密的一次談話中可以知道。
1993年,李安拍的《喜宴》,在“柏林影展”中與中國內地影片《香魂女》同獲最佳影片“金熊獎”。 李安打電話回紐約家裏,接電話的正是他太太林惠嘉。李安(十分高興):“我得獎了!我得獎了!得了最佳影片金熊獎。”
太太:“哦!”
李安:“我的《喜宴》和大陸影片《香魂女》並列最佳影片!” 太太:“哦!這個影展是不是只有華語電影參加?”
無用之人所做無用之事,李安成事了!
李安的作品一如他的為人,平淡中自有真味。恰似白居易的詩,人人能懂,從不艱澀,更不弄玄虛,卻絕不淺薄低俗。1993年《喜宴》代表“中影公司”得獎,加以1991年的《推手》獲“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及“金馬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一時間,他成了“中影公司”的鎮家之寶。
譽之所至,謗亦隨之。他的風頭之健,當然超越了臺灣許多導演,遂也引發了一批影評人對他的批評(姑隱其名),甚至說他的作品毫無藝術價值。這時候,就可以見到他人格上的特質了。他在面對這些批評時,出奇的平靜,而且自始至終面帶微笑,不以為意。
在電視臺接受訪談時,主持人念了一段別人發表在報刊上批評他的文章,問他有什麼看法。只見他笑笑說(大意):“無所謂。看到或聽到這些批評,反而讓我覺得大有可能,因為還有很多值得努力去改善的空間。”
他為自己的創作定位,甚至說出“無用之人所做的無用之事”。這種胸襟與大度,放眼內地、香港、臺灣,真是找不出第二位。早期跟過他到紐約拍片的班底曾透露,李安是個愛家的男人。拍戲時不管幾點鐘收工,他一定回家陪家人,很少與工作人員去買醉作樂,徹夜不歸。他對家的重視與定義,與許多電影工作者不同。這種觀點呈現在生活中,也反映在作品中,從《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以降,乃至到好萊塢拍的《理性與感性》、《冰風暴》,甚至是同志電影《斷背山》,都反映出他一以貫之的對家庭的重視。這種對“家”的觀念,不正是中國社會自古以降的倫理觀點!說李安很“中國”,是絕對沒有人反對的,包括老外。
誰說不能拍一部尼姑、和尚談戀愛的電影?
李安在《斷背山》勇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他的母校(也是我的母校)“臺灣藝術大學”(我們就讀時叫做“臺灣藝術專科學校”),要頒給他“博士學位”。姑不論“台藝大”能不能頒這個獎(畢竟已經引起了一些口水與爭論),但李安已初步婉拒了這項錦上添花之舉。曾經在“台藝大”擔任過“影劇系”系主任、教過李安的顧乃春老師,就對我說過,李安成名後回學校,面對著一群“菜鳥”學生所提出來的不成熟問題,從來沒有表現出一絲的不耐,總是耐著性子、面帶微笑,盡可能去回答學生們的問題。
對於李安當年在學校求學的過程,顧老師坦言因年代已久,不復記憶。對於當時李安在學校時,有沒有與哪位女同學要好過,顧老師說:那恐怕只有問他本人才知道。但顧老師對李安有一項較深刻的印象,則是記憶猶新,他說李安長於思考,做事認真。
那時候“影劇科”分“電影”與“戲劇”兩部分,電影的課多一些,但戲劇部分,則因為有舞臺劇的演出,具有實驗性質,同時也可以具體驗證理論。但一般學生大多偏重“電影”的課程。 顧老師說,李安不管是電影的製作或舞臺的演出,都十分認真,一絲不苟。有一次出去表演,觀眾反應冷淡。返程中,李安向顧老師談道:不管觀眾反應好或壞,都是很重要的。舞臺上的演出者應該與觀眾互動,才能產生共鳴。
這一段談話,讓顧老師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對這位平常木訥寡言的學生,有了特別的看法。顧老師還特別談道,有一次李安回學校演講,一再強調“題材”的重要性,告誡學生最忌“曲高和寡”,但是要勇於思考及突破,譬如:尼姑、和尚不能談戀愛,但誰說不能拍一部尼姑、和尚談戀愛的電影呢?
西部牛仔的同性之戀,美國電影極少碰觸,李安卻拍了!而且得到了全球的公認。誰說和尚、尼姑不能談戀愛?
李安,同志?徐立功:無聊!
在“李安現象”發燒了一個星期之後,雖然電視節目中,還有些零星的報導,但都側重在他會不會拍《臥虎藏龍》前傳?會不會再與章子怡合作? 甚至還有好事之徒,說李安自《喜宴》到《斷背山》,老愛拍“同志”題材,可能自己也是位“同志”。最後衍生成:“斷背”其實是“斷臂”,就是中國人所謂“斷袖”之意。荒唐到了極點,引來了中影公司前老總,也是李安的“伯樂”徐立功的出面澄清,說李安絕不是同志!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可笑、更無聊的?“中影”之于李安,或縮小範圍來說:徐立功之于李安,其關鍵性或重要性,眾所周知。若非《推手》與《飲食男女》、《喜宴》讓李安嶄露頭角,豈能有今日?
但是,幫“中影”拍過戲的導演,不下數十,李安卻只有一個。除了先天的條件,與時空的配合,加上自身的努力,與個人的特質,方有以致之。
中國人常說:由小看大、見微知著。
李安今日成就的構成,涵蓋了一切好的與壞的,包括他兩次大學考不上,只好去國立藝專學電影;在紐約沉潛了六七年,無所事事卻蘊積了能量;也包括了他家人對他的包容,以及所有的機遇。先天人格的特質、後天謙和的態度與不懈的努力,都是關鍵。這裏面,少一味都成就不了李安。
不過,我們要傷心地說:“中影公司”已經沒有了!臺灣電影也幾乎等於沒有了!此時還能奢言什麼第二個李安的來到?
主題:金馬獎秘書長解密李安 幾十年細說從頭
無圖示
Akina
文章日期:2006/3/17 21:02
文章點閱:1599